元界财讯2025年09月19日 22:21消息,电影《闯入海岛》两岸青年导演抓住时代风潮,展现新锐力量。
9月5日至7日,第五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举行。主办方供图

出租车驶向福建平潭岛,车内循环播放着一首流行的说唱歌曲。司机突然问道:“你知道《大展鸿图》吗?”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出租车成为了一个微小但充满故事的空间。车内的音乐往往反映着时代的脉搏,而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对话,则可能不经意间触及一些热门话题。像《大展鸿图》这样的作品,无论是在网络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可能成为人们交流的共同话题。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对积极向上、充满希望内容的向往。这种共鸣,或许正是流行文化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

副驾座上,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导演冯于伦并未听过这首歌。9月上旬,他正携短片《海浪》前往第五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的活动现场。途中,司机与他聊得十分热烈。他觉得这一场景宛如电影中的画面,“台湾与大陆,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这种碰撞产生的火花非常美丽”。

关于“碰撞”,影展创始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洪雷回忆起一个意外的场景:9月5日,百余位青年创作者在一家火锅店的二楼聚集,围坐了十几桌。来自大陆、台湾以及海外的创作者们,各自贴着自己的名字,面对面进行交流。“让不同地区的人有机会相聚,就是我们最大的意义。”洪雷表示。
人们提到平潭IM影展时,往往会关注两个方面的“年轻”:在本届影展中,“24”这个数字被反复提及,这是主竞赛单元参赛作者的平均年龄;而从影展本身来看,尽管仅走过五届历程,但已累计收到12705部参赛作品。
洪雷回忆起第一届活动时的“业余”状态,当时电影放映并非在影院,而是在会议室里,观众们坐在太师椅上观看影片。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烦恼不再是担心没人来参加,而是“预约满了怎么办”。 从最初在会议室里简单的观影体验,到如今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盛事,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活动影响力的提升,也反映出公众对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种从“冷清”到“火爆”的转变,既是组织方努力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氛围逐渐升温的缩影。
影展举办的那个周末,电影如“闯入者”般进入平潭,为本就热闹的海岸注入了鲜活而自由的情绪与声响。 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刻,电影不仅带来了艺术的共鸣,也让原本宁静的海边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这种文化与自然的交融,让整个城市在短暂的时光里被赋予了更多层次的表达。影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放映影片,更在于它成为连接人与环境、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梁。
一群平均年龄24岁的电影人剖析自己
看50部主竞赛入围作品前,影展终审评委会主席陈冲曾猜测,或许有些短片会让她觉得时间“难熬”;但实际观看过程中,她目不转睛地看完每一部,“非常惊喜”。 从陈冲的反馈可以看出,尽管她最初对部分作品抱有保留态度,但最终仍被其内容所打动。这不仅体现了这些短片的高质量,也反映出评审在专业视角下对多样性和艺术表达的包容与认可。观众和评委的期待往往存在落差,而这次的结果证明了创作者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观众在挑选印有影片海报的明信片。陈宇龙/摄
“电影的一个很大作用,是为你搬来另一方水土。”陈冲入行已经50年,她始终以一种好奇的心态参与评审工作: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面临怎样的困惑,又在思考什么,对未来又有什么期待? 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情感的共鸣。它能够打破地域与时间的限制,让观众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正如陈冲所说,电影就像是一扇窗,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而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电影所承载的意义也愈发重要。年轻一代在面对社会变迁、价值多元和信息爆炸时,他们的困惑与探索值得被关注与理解。而电影,正是回应这些思考的一种方式。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陈冲语气柔和,语速适中,表达清晰而有条理。她并不倾向于为这批青年电影人总结出一种统一的风格,而是更关注他们作品中展现出的多样魅力,希望这些创作者能够保持自身独特的个性,就像他们的“签名”一样,不被同质化所淹没。 在我看来,青年电影人的成长需要更多包容与尊重,他们各自的艺术表达方式正是这个行业的活力所在。与其强求一致,不如鼓励他们坚持自我,让不同的声音和视角在银幕上绽放。这种多元性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生态,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和《后来的我们》的编剧袁媛在谈及对新一代电影人的观察时提到:“他们更倾向于关注自身,讲述更多关于‘我’的故事,包括‘我’的迷茫、‘我’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在虚拟或现实世界中的身份认同。这种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让我深受触动。”
在台湾艺术大学读研的冯于伦,创作的《海浪》虽然讲了一个关于出狱者重新认识世界的虚构故事,灵感却来自上大学后对父亲的观察:对新事物感到陌生、不会用智能手机。拍摄完成不久,父亲过世,冯于伦突然觉得自己从故事的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他在影片中讨论死亡议题,认为年轻人的视角同样重要,“每个年纪对于生死的感悟都不一样”。
陈冲告诉记者,“我”的视角是很多青年导演在创作第一部影片时的偏好:选择记录某一件改变自己人生的往事,一次“生命中非常重大的体验”。记者在参与一场主竞赛入围作品展映时也发现,3部影片都是毕业作品,且都是由创作者亲身经历改编。
其中,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青年导演李新宇带来其执导的影片《穿过公园就到了》,“公园”指的是千禧年的国企生活区。李新宇很认同陈冲的总结:“我们年轻的导演,确实得花不少钱,肯定希望能把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事情,用短片这种媒介去表达。”有人在看完《穿过公园就到了》预告片后很有兴趣:“是时候该讲讲00后的成长故事了。”
父母来自不同省份,童年又在多个城市间辗转,李新宇从未掌握任何一种方言,始终觉得自己像个没有故乡的人。当同学们选择回到家乡完成毕业作品时,他却将目光投向了曾经与姥爷一同生活过的国企生活区,“那里或许能带来某种类似故乡的联系,希望它能成为我情感深处的出口”。 在我看来,这种对“故乡”的追寻,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探索。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经历着流动与迁徙,传统的地域归属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复杂的情感联结。李新宇的选择,反映出一种对过往记忆的珍视,也揭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渴望。他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宿。
在展映现场,官方免费提供的影片周边产品就像一个隐形的“投票场”。在所有影片放映前,来自各地的影迷聚集在一整面明信片墙前,收集印有特展和各单元入围影片海报的明信片,一名影迷形容这是一种“抽盲盒”,“先抽再看”。《穿过公园就到了》的明信片上印着一片老式游乐场元素的气球——它是主竞赛单元最早被“抢”空的。
希望平潭“给我一股风”
在青年电影之夜上,中国香港知名摄影师鲍德熹即将宣布本届影展的“麒麟评委会选择”——一项奖金为25万元的荣誉。当他说出“我要用广东话念出这个戏的名字”时,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观众反响热烈。 这一细节不仅展现了对地方文化的尊重,也反映出影展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用广东话公布奖项名称,既拉近了与本地观众的距离,也让文化多样性成为活动的一部分。这种细腻的安排,让影展不仅仅是电影的展示平台,更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获得“麒麟评委会选择”荣誉的《紫菜》,导演梁紫茵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她的影片拍摄于家乡广东佛山。除了方言,她还特别向记者提及,片中常年葱茏青绿的树木也是家乡的特色。梁紫茵坦率表示,除了感情使然,家乡也为创作提供了实际的便利:地方文化、氛围营造、时代背景——这些对创作者来说都相对熟悉。
获得本届影展“麒麟评委会选择”荣誉的《紫菜》放映结束后,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主创团队在现场合影纪念。陈宇龙/摄
在台湾,冯于伦发现很多创作都围绕着生活场景,连接观众的是一种对他们所身处城市的情怀,“好奇在城市场景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但这其实也与拍摄条件相关,冯于伦在平潭看到了大型影视基地,这样“资源整合”的拍摄场景,在台湾并不多见。
吉林长春导演姜柏廷拍摄的长片《小径分岔的花园》,同时涉及家乡和她的“福地”平潭。该片是平潭IM影展人才培育体系孵化的首部长片,曾获评第二届影展的麒麟优秀短片,长片项目则在第三届影展生生不息成长计划获得最佳提案。“我作为青年导演,从有想法到写剧本,到参加创投、找投资,应该算是经历了一个很标准、很完整的过程。”
她的影片被寄予厚望,“我也很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榜样,但是我不追求成为大家的标杆,只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创作者看到,是可以被做出来的,只要你坚持努力,哪怕3年、5年,它是有机会能做出来的”。姜柏廷觉得,《小径分岔的花园》作为一个青年影展孵化的影片,她做的很多表达上的创新尝试也被充分尊重。
在青年电影之夜现场,姜柏廷表示,她收到了来自导师和学员的许多反馈,希望她能进一步完善影片的后期制作。她也期待平潭能给予她一股风,带来灵感。当晚,平潭的海风强劲,不断将她的长刘海吹起。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姜柏廷对作品的打磨态度认真,同时也表现出对自然环境与创作灵感之间关系的敏感。平潭的海风不仅是物理上的存在,更可能成为她艺术创作中的某种象征。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往往能激发出更深层次的创作动力。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外部环境与内心感受的结合,往往是推动作品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
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举办第一次产业放映前,平潭下了一场小雨,搭载记者的出租车司机透过窗上的水滴,看见影院门口热闹的人群。这是他在平潭第一次遇到非体育赛事的大型活动。司机发表评论:前阵子平潭旅游人气很旺,那些外地来的年轻人肯定也对电影感兴趣。
从这届开始,影展名称中加入了“平潭”二字,使电影与这座岛屿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军在影展期间向媒体表示,计划为影展打造一个永久性的举办场所,拟建设“平潭海峡两岸电影宫”,以进一步提升影展的品牌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AI短片像浪潮一般打来
上文提到的影展明信片墙上,某套明信片的清空突然提速,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影片完成放映,成功“击中”了一些观影者。9月6日晚,一名影迷就向同伴惊呼:“机器人的那个片子,没了!”
这名影迷说的是“未来已来·AIGC”单元的入围短片《电火花之舞》,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创作者杨力鉴获得“最佳AI创作者”荣誉。这部影片大胆设想,在未来世界里,机器人如何靠读取人类的经典电影来理解、获得爱情。“爱和电影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创作团队的这句话成了映后分享现场的金句。
“未来已来·AIGC”单元入围作品放映后,主创上台与观众互动。陈宇龙/摄
开启AIGC征片,是这个年轻的影展又一次“打破边界”的尝试。国内外知名电影节在近两年开始尝试设置AIGC竞赛单元,法国在今年4月举办了首届世界人工智能电影节,而本届平潭IM影展收到3443部AIGC短片投稿。AIGC单元评委崔伊形容,“一股非常大的浪潮涌来”。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片人王安忆在主持AIGC影片映后交流活动时,向每位创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你们的作品完成至今有多长时间?是否发现作品中的某一部分因为技术进步而有实现重大突破的可能?”随后,王安忆进行总结,表示大部分作品都是近期完成的,实拍作品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同时指出,实拍作品难以像AIGC那样,在短短一个月甚至一两天内就迎来关键技术的突破。
影展组委会被投稿创作者的多元身份打动:算法工程师、退休工人、动画专业学生、烧烤师傅、染织设计师……在崔伊看来,AIGC为创作者争取到了“表达平权”,成本大幅度降低。设置AIGC的竞赛单元,是考虑到“工具的能力还有限,所以要把它区别对待”。但他相信,在一两年之内,“它就可以跟上成熟影视作品的脚步”。
AIGC的出现似乎也在悄然改变着电影节原有的秩序。例如,一些作品的映后交流环节更像技术论坛或答辩现场,其中两位入围作品的创作者耿瑞阳,在交流中被观众问及“如何保持人物一致性”的问题,反映出观众对AI生成内容在叙事逻辑上的关注与质疑。 这种变化显示出技术对传统影视创作和展示方式的深度介入,也促使创作者在表达方式上做出调整。当技术成为创作的一部分,观众的期待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不仅关注故事本身,也开始关注背后的技术支撑与逻辑合理性。这或许预示着未来电影节在内容呈现和互动形式上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与机遇。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联合导演范铭当天在后排看完全片,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也在尝试用AI技术与纪录片结合。她承认看大量AIGC短片会陷入一种在世界观、技术上的疲惫,“最后能沉下来让人记住的,往往是与人类内核最靠近的部分”。
这与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制作系主任杨树的评审体验不谋而合。他认为,真正的“破壁者”需要同时在技术和艺术上达标。实拍与AIGC之间共通的是创意与视听语言,即“如何用画面和声音来讲故事”“评价一个片子的质量,核心还是会回到它的创作上”。
耿瑞阳说,现有的AIGC话语体系里,“很多观众是被忽略的,很多创作者是没有被点燃的”。这次入围的两部影片《沙漠之歌:拉提法》《东海暗夜:1920》,分别讲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关村创业的故事。“关于太空、战争的AI影片比较多,我们在寻找另外的题材和话语体系,AI影片的天花板是不是不止于此?”
李新宇也曾创作过AIGC短片,探讨的是AI在生成内容时本身有没有情感,“是不是也着急下班想去喝杯美式”。不过,使用AI的经历让他更清楚了自己对真实影像的追求。他决定,接下来还是要去拍纪录片,“镜头代表着我的眼睛和手,要去触摸、感知这个世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陈宇龙记者蒋肖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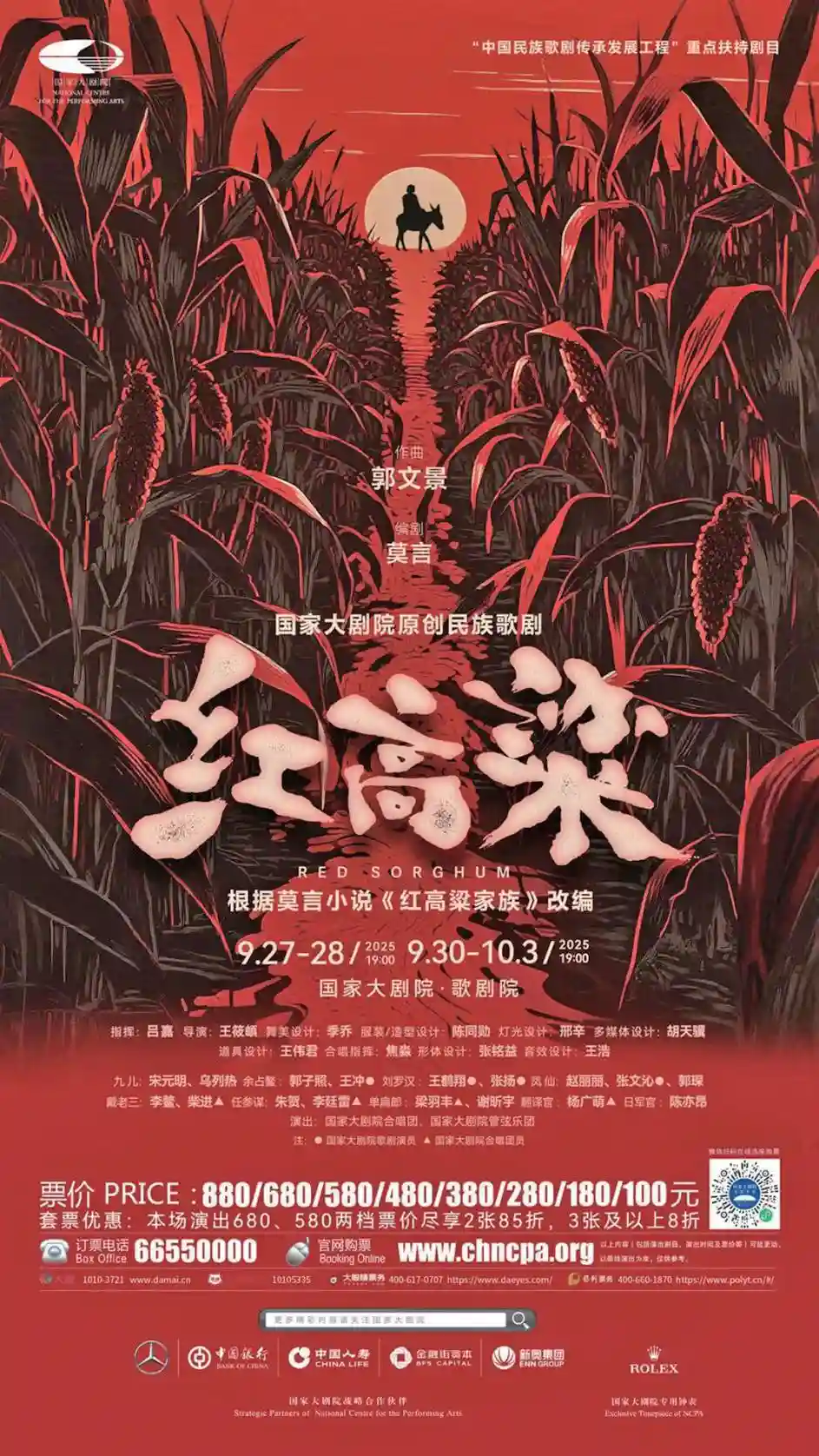






























留言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暂无评论,成为第一个评论者吧!